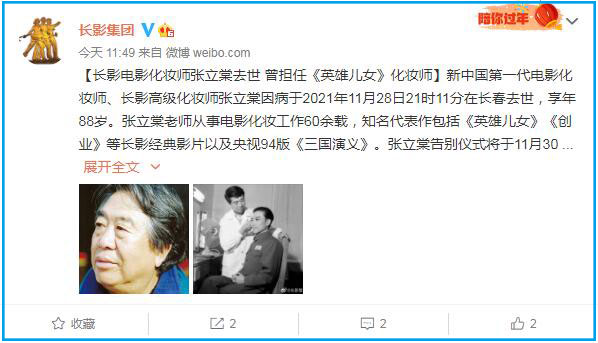爱在人间
三叔名叫叶召普,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房哥哥,因为排行老三,所以我从小就叫他三叔。三叔一生孤寡,在我们当地算得上远近闻名,虽然已经去世几年了,但我对他的印象还是记忆犹新,而且时不时会想起他来。
听父亲说,三叔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,在姐姐和邻居的拉扯照顾下,才得以生存下来。我小时候,三叔还是壮年,他个子不高,体态偏胖,圆圆的脸上透着营养过剩的油光,再加上那浓浓上扬的三角眉和粗声大气的说话声,总显出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。因为秃顶,头上永远都戴着一顶蓝布帽子,由于长时间没有换洗,帽檐总是油腻腻地,背地人送绰号叶秃子,但谁也不敢这样当面叫。可能是秃顶的缘故,他一辈子没有娶媳妇。我记得最初他住在两间土坯茅草屋里(那时农村基本都是茅草屋),一次在冬天烤火取暖时,不小心被烧掉了。当时,生产队把他临时安置在村南头集体的三间直通大瓦房里,生产队开会、分粮也在这屋里举行,结果他就住下了,直到后来离家出走。那个房子也就空下了,因长期无人管理后来倒掉了。
在大集体时,所有棒劳力都在生产队干农活挣工分,三叔却经常被生产队派出务工俭勤。因为他一个人,家里无牵无挂,乐意外出游荡。每次从外面回来,都是衣着光鲜,神采飞扬,在大人小孩的簇拥下,滔滔不绝讲一些外面看到或听到的稀奇事情,令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人感觉无比向往。三叔是个爱听奉承话和极度虚荣的人,为了炫耀,他是本村第一个戴上手表的人,特别是在大冷天里,时时撸起衣袖,煞有介事看看手表,后来我才知道,他其实并不认识手表上显示的时间。还记得在一个夏天,三叔带回一个砖头大小的收音机,每到傍晚,就把收音机放在村边的打谷场上,再把声音调得大大的,惹得本村的大人小孩们早早聚到一起听广播,听到入神处,为了吊起人们的胃口,他就故意调调台,或称没电了,让人干着急。每当这时,三叔看着人们那诚惶诚恐的样子和乞求的眼神,就得意地笑了,再故作姿态把声音重新调好。确实,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前,三叔算得上全村最自由和最富有的一个人,是典型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享乐主义者。在我幼年的心灵里,对他是不无崇拜的。
实行分田到户后,农民终于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,可以自由地种植各种农作物,粮食产量得到很大提高,剩余劳力也得到解脱,大批农村人开始走出去,闯荡外面的世界。三叔也不例外,他本来就自由散漫惯了,生产队给他分了两个人的田地,却一直撂荒着,门一锁,招呼也不打一下,就到外面务工去了。就这样,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他再也没回来过,家里的田地邻居帮种着,代缴着各类三提五统和税收。在这期间,村里的父辈们时常代人捎话给他,说家里生活水平提高了,让他回来居住和创业。但他却一直不愿回,并放话回来说,何处黄土不埋人呀。渐渐的,人们淡忘了他,就像他家倒掉的房子一样,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2007年的仲秋时节,天气微凉,乡村里的庄稼基本收割完毕,到处是一片丰收和谐的景象。突然有一天,村部接到一个外省打来的电话,电话里说我村有个叫叶召普的人,在他们那里打工,现病得很重,快奄奄一息了,让我们这边赶快派人接回老家,以便料理后事。对这个失联多年的人,叶氏家族有人提出异议,认为在辉煌时忘掉了家乡,在穷困潦倒时被人抛弃,才想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,对这种人应该不予理会。但在村委会和大多数自家人坚持下,还是商定把他接回家里,替他治病和解决一系列吃住问题。于是,在第一时间里,我看到了他,与我儿时印象中的三叔有着天壤之别,只见他衣衫褴褛,面色黑乎乎的,像半年没有洗过一样,头上也没有戴帽子,稀疏的几根头发耷拉在发黄的头皮上。看到我,他嘴角翕动了几下,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,枯涩的眼光满是祈求和无助,并极力地想从一捆破棉絮上站起来,但始终没有如愿。听别人介绍,他患有严重的类风湿和高血脂病,现在已经无法站立了,行动只能靠屁股挪动。唉,这就是我幼时心目中崇拜的三叔吗,现在竟落得如此狼狈不堪。即便如此,我们还是用架子车把三叔拉到邻居家两间闲置的旧瓦房里,为他准备了生活用品。此后,本组村民开始自发行动起来,年龄长一点的男人经常为他更衣擦洗身体,妇女负责洗衣送饭,年轻人为他请医治病,管理处党委和村委会也及时筹措资金,新建了两间砖瓦房,置办了家庭所需用品,使他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。就这样,在社会各界的悉心照料和帮助下,三叔半年后又能下地行走了,而且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了。
为了减轻政府和邻居的负担,在三叔的一再要求下,村委给他找了一份工地看场的差事,挣一些钱补贴家用。从此,三叔的脸上开始漾满了笑容,面色也红润起来,以前暴躁的脾气也改了不少,见了每个人都热情地打招呼,诉说党和政府的关怀,夸邻里乡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,有时也买一些小食品,分送给邻里孩子。因为他是孤寡老人,每逢年节假日,本组邻居都争着接他到家吃饭,不让他有孤独和失落感。到了2015年,国家开始实行精准扶贫,三叔又被村民理所当然评为五保贫困户,享受更加细致的照顾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三叔不注意身体,又爱吃猪肉,致使高血脂再次复发,2016年3月,在邻居和本家的守护下,三叔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充满爱的世界,享年72岁。在村委会主持下,本组村民给他体体面面办了丧事,立了墓碑,每逢清明和正月十五,都会给他扫墓和送灯,以示怀念。
三叔安详地走了。我想,他走的时候应该没有太多遗憾,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,特别在他晚年回到家乡的近十年间,生活是幸福的,他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和人间的大爱。(叶先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