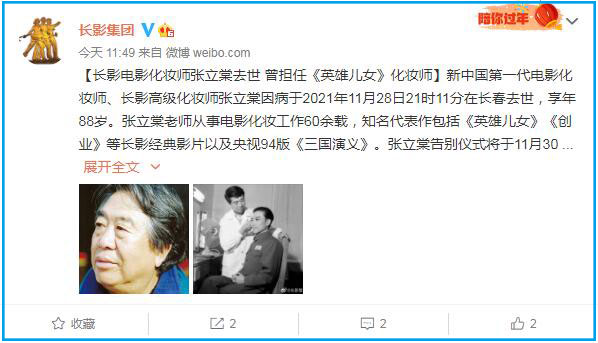制度史的“生命”所在
制度史的“生命”所在(主题)
邓小南
钱穆先生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一书中,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,也就是说,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。对于“制度”,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。大致上讲,可以说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,是制约政治活动、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。
有学者强调:“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、功能和形式,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,是制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。”也有学者指出:制度分为“无意中逐步形成”和“有意建构”的两种类型,即一类是“经历长久,约定俗成,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、伦理、信仰、仪式、节庆等”;另一类是“为特定需要、目的(如政治、社会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等),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、标准和程序(如地缘、血缘、财富、才德能力、意识形态、公民大会、议会、乡举里选或科举等)而有意建构出来”的多重秩序网络。不管是活在今天,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、空间里,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,而不是在某种单一秩序里。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,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,是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。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。我们判断一个国家、一个政权、一种体制,其走势是否适合于文明进程,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。
我们知道,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,有它的节奏、韵律,历经形成、生长、发展,可能不断完善,也可能走向衰亡。追踪、观察、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,正是制度史的“生命”所在。
当说到制度、规则的时候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。但是,如果承认只有在“运行”之中,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,我们就会注意到,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、流动的现实。因此,制度本身的恒常,它所追求的“可预期”,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,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,或者说构成有张力的两端。在这种情况下,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,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。
所谓“非正式”,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,“令式之外”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。一方面可能是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,或是应对制度“形式目标”的要求;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些调适甚或扭曲。唐高宗巡幸洛阳前,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:“关中之事,一以付卿。但令式跼人,不可以成官政,令式之外,有利于人者,随事即行,不须闻奏。”短短数语,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令式之外的可能性。欧阳修在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:一种是“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”,另一种则是“事虽非正,后世遵用,因仍而不能改”。从积极的方面讲,这些“事虽非正”的运作,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;在某些情况下,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非正式制度的“因仍”“调和”才得以推行。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,那么几乎可以说,“正式”与“非正式”交错混糅互为所用,并非截然二分,甚至是相辅相成的。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,存在一定的空间,空间里面有变形,有扭曲,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;这种空间中的活动,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,也可能带来制度“平稳有效”的感觉。
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,应该清楚,自己口中、笔下的“制度”二字,指的是书面规定,还是现实运行;二者从来不曾隔绝,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。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,有些研究,“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,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”。我们现在讲制度,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,其实有同样的问题。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、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,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“整理”,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。
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,包括我自己在内,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,而人为因素是一时、偶发的。实际上,制度本身从来都是“规范”和“人事”折中的结果。制度本为“设范立制”,既是引导、保障,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,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。这样的引导、限定与制约,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曾经生效?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、修正、抵制,这些“人事”起到什么作用?都需要通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。
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“人”赋予的,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。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命力,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。所谓“活”的制度史,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,更重要的是指从现实出发,注重发展变迁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。
(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