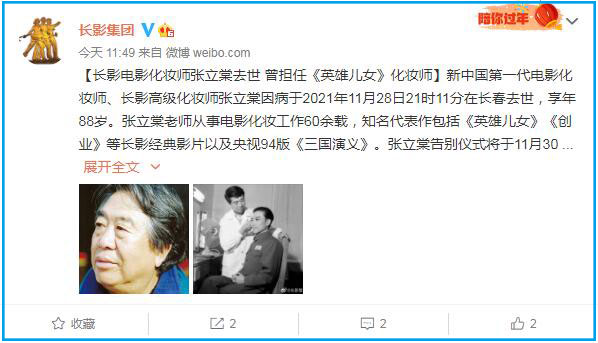“90后”的考古现场
北京日报记者 李祺瑶
从北京市区一路向西南40余公里,抵达房山区琉璃河镇董家林村,沿着林间土路步行,入眼是一排临时搭建的“神秘”大棚。这里,便是“北京城之源”琉璃河遗址的发掘现场。
进入棚内,别有洞天。一处处西周早期墓葬被逐一揭开面纱:编号为M1901号的墓葬曾出土迄今为止北京地区最大的青铜器堇鼎,M1903号墓葬则是首都博物馆“镇馆之宝”伯矩鬲的发掘地。时隔40余年,两座大墓重启发掘,一批新发现再次吸引世人目光。而在这两座墓葬之间,一处新发掘的M1902号墓葬被“破壁”呈现,精准还原墓室内一棺一椁……
“这片祖先留下的遗迹,总能带给我们惊喜。”站在墓葬边,“90后”姑娘王晶脸上笑意盈盈,一副秀气的细框眼镜,与常年风吹日晒、微微起皮的脸颊形成鲜明对比——作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琉璃河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,她从2018年研究生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琉璃河遗址,在2019年至今开展的新时代琉璃河遗址考古与研究工作中,与她同行的还有两位“90后”女队员安妮娜、盛崇珊。凭借最新科技手段和文保技术的加持,这支年轻的考古队伍在黄土深坑中小心翻找,细细收集着古人遗留的蛛丝马迹,一点点拼接复原历史的碎片,为北京城寻根溯源。
❶
发掘车马器如同“开盲盒”
考古现场,一处巨大的墓坑格外显眼,从地面向下望去,大约有4至5米深,经过一段台阶向下到达二层平台,再往下的墓壁上搭着一段木梯,直达墓底部,仔细看,墓底还有少量积水。
“这就是我们这次发掘的M1901号墓,其实,它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——上世纪70年代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发掘的253号墓。”墓坑边,王晶向记者介绍,40余年前,这里出土了现存已知北京地区最大的青铜器堇鼎,因为当年地下水水位较高,墓葬没有发掘完整,“在老一辈学者的指点下,我们了解到在这座墓葬下面很可能还有一些没有揭露出来的细节。”
为此,2021年秋,考古工作者重启了对这座墓葬及周边相关墓葬的发掘工作。
如何降水,是王晶和同事们最先面临的问题。琉璃河遗址位于房山区大石河畔,地势较低,地下水源相对充足,地下水位较高。“地下一米多就见水,给发掘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。”王晶说,她们联合降水专家,对墓葬周围进行了地质结构勘察,在墓葬四周安装了排水管,一边抽水,一边发掘。临近寒冬,为了在结冰冻土前抓紧时间获取更多信息,三个姑娘经常加班到深夜,在淤泥里一点点清理发掘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,发掘工作初见眉目。“我们提取到几片青铜车马的小构件,这种情况在发掘过程中挺常见的。”王晶回忆,当时她和同事认为这只是一些散落的构件,但随着夯土一层层被清理,一个个青铜构件的“面纱”也被揭开:有圆形、方形、半月形……这些小部件之间,似乎能够连接相扣。她们立马“收手”,彼此迫不及待地分享心中的喜悦:“开盲盒开出‘隐藏款’了,这很有可能是一套车马器!”
考古发掘的思路也就此转变。“我们不再把发现的器物单独提取出来,而是对这一区域进行整片清理。”王晶解释,虽然这些器物比较小,但是每件器物都有自己的相对位置,可以清晰辨别,它们在下葬时就是原状保存的:比如成对儿的马衔和马镳都是环扣在一起的,在马脸颊两侧的位置;还可以看到革带上嵌着的青铜饰件,就是以带状保存在原位的,可能直接连到马背控制缰绳的地方。“这是非常难得的,通过研究器物的摆放位置,我们可以更精确地复原马身上缰绳的位置,了解3000年前的古人是如何御马的。”
经过整片清理,王晶和同事们共发现了4匹马的马器,为了保持这些器物复杂的位置关系,便于后续的实验室研究,她们决定对全套车马器进行整体套箱提取。
“这是一个长、宽均为1.6米左右的正方形空间,体积大、重量沉,又处在淤泥之中,按照常规办法以套箱的方式提取难度很大。”考古队员盛崇珊专攻的领域是现场保护,她解释,套箱提取是设法从土里在文物四周套上木板,将文物“打包”取出,一般会以钢板作为底板对箱子进行承重和加固,如何在泥里顺利插入钢板,成为她们要解决的难题。
接下来四五天的时间里,王晶、安妮娜、盛崇珊三人一遍遍尝试,最终在专家的指导下,找到了最佳方案——用千斤顶从水平方向将钢板插入泥土中,四周用钢棍吊着铁丝以确保钢板不往下陷,从而将整套车马器成功提取出来。尽管三人此前都有过套箱提取的经验,但是面对不同的文物、不同的环境,“每一次都是独特的新挑战,每一次都要迎难而上。”王晶感慨,能够在没有伤及周围其他文物的情况下,将车马器整体套箱提取,且结构基本没有变化,花费再多时间也是值得的,“这套车马器的发现,也提高了我们对墓主人地位和等级的认识。”
❷
首创“破壁发掘法”
墓葬的细节也被考古人员精准还原。M1901号墓不远处,一座长方形的墓葬清晰呈现——由内向外,一棺一椁“划”出墓葬的两层“边框”;墓葬中央,墓主人身上遍施朱砂,身旁和头顶,大大小小的器物错落摆放,从土层中露出青绿色……此处就是新发现的M1902号墓。
与M1901号墓相比,M1902号墓的面积、规格都小了不少,“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抱着‘挖大墓’的心态。”王晶打趣道,真正开始发掘,她们才发现,这座墓“麻雀虽小五脏俱全”,“现场出土的器物组合丰富,包括铜器、漆器、陶器等,而且上下叠压关系比较复杂,在棺外和棺内都发现了动物骨骼。”
如何还原墓葬中的层层细节?一开始,王晶和同事们在墓圹上方横向搭起垫板,趴在墓上方进行清理,王晶一边干一边思考:靠近墓框边,棺椁的结构是最不容易判断的。能不能转变一下思路,在从上向下发掘的同时,从墓室侧面向内发掘?这样更方便发掘,也更易于观察。为此,考古队员们参考了其他墓葬的发掘方案,请教了相关领域的考古专家,创新出一种颠覆常识的发掘方法——破壁发掘法。怎样给墓室“破壁”?王晶打了个比方:“就像切蛋糕一样,我们将墓圹一分为二,沿着中轴线破开墓室外东侧二分之一的部分,从椁室之外向内清理,这样墓葬就呈现出一个清晰明显的剖面。”
方法的创新,也让队员们有了新收获。对重要遗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清理的同时,她们还留取了重点痕迹剖面的影像和图纸资料,清理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、织物交叠现象,辨识出多处木质遗存、席纹等,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早期带纹饰的丝织品,精准还原了每件出土器物的空间位置,“从外向内,由椁室到棺,完整揭露了西周时期的下葬过程,为我们还原当时的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材料。”王晶说。
在M1902号墓葬出土的文物中,考古队员们也收获了一些“小惊喜”。
在一套青铜尊、青铜卣和青铜爵组成的青铜礼器组合中,一件青铜卣中的铭文为:“太保墉匽,延宛匽侯宫,太保赐作册奂贝,用作父辛宝尊彝。庚。”根据铭文,队员们推断其大意为:“太保在匽筑城,遂后在匽侯宫举行祭礼。太保赏赐给作册奂贝,奂为他的父亲辛做了这件礼器。庚。”王晶解释,这段铭文最重要的地方在于“太保墉匽”4个字,证明了3000余年前,周王重臣召公亲临燕都即今天的琉璃河燕都遗址所在地,建筑了燕国都城城墙,“也许这座墓的墓主人并不是一个名留青史的人物,但是因为他记录了这件重要的史实,为这座墓葬赋予了更深刻的内涵。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认为,这件器物铭文上无可争议的文字资料,实证了3000余年的北京建城史,在世界城市史研究中具有独特价值。
不断“拆盲盒”,为历史“拼图”的过程,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,更难能可贵的是始终保持一颗热情而富有创意的心。
王晶喜欢的一个词是“地”道酬勤,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毕业后来到琉璃河,近四年时间里,她一直在实践中“补强”,让考古从书本里“走”出来。如今,这个文质彬彬的小姑娘,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考古队长,“考古现场,每一个新发现都是独一无二的,我会尽力为它设计一套专属的发掘和保护方案,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”
❸
“文物医生”与“技术咖”护航
考古发掘现场,文保技术和现代科技也会密切绑定,全程跟进。
墓葬被打开,文物表面的土层被去掉的一刹那,盛崇珊的工作就开始了。去年从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专业刚毕业,她就来到琉璃河当起了“文物医生”。在发掘现场,她总是拿着各种药水,趴在地上,第一时间对文物进行保护。
文物出土后的保护修复需要“慢工出细活”,盛崇珊却快人快语,“文物保护也慢不得。”她举例说,在曾出土伯矩鬲、现编号为M1903的墓葬中,这次新出土了多件漆器,包括三角纹簋、豆等,“这部分漆器的保存状态不是很好,被发现的时候,这些器物内部的木胎已经不在了,只有漆皮的结构存在。”什么样的化学试剂能让这些漆器保持出土前的最佳状态?盛崇珊反复试验,终于找出解决之道——采取薄荷醇、石膏、聚氨酯发泡剂等,结合整体套箱快速提取,将漆器迅速置入实验室,再进行研究和保护修复。
目前,盛崇珊和同事们正在实验室里对这些漆器进行逐块拼对,努力复原器物原本的样子。针对不同材质的文物,她们会进行因地制宜的保护,对木杆、席痕、朱砂、织物等有机类文物,使用薄荷醇等进行临时加固处理;对青铜器则用手术刀进行“机械清洗”,使用保护性化学试剂涂在器物表面形成“保护膜”,再对磨损的器物进行拼接黏合。
与文保同步,科技赋能,让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范围有了新认知。
安妮娜是考古队里的“技术咖”,专攻数字化空间分析。2019年,原本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工作的她,听王晶透露要建GIS地理信息系统,就毫不犹豫地来了。调查勘探、数字化绘图、拍照,三维建模,调试、优化系统……她经常在发掘现场和实验室两头跑。像绘图、拍照这样的工作也会有在读的大学生来帮忙,但安妮娜总有“操不完的心”,每一个细节都亲自把关。
如今,安妮娜制作的系统界面里,大到一座灰坑,小到一个陶片,所有信息都被收录在一个三维的立体“地图”中。“对目标进行空间分析,我们甚至可以通过采集到的植物和动物样本,知道哪个地方农作物多、哪个地方家养的兽骨多,进而了解古人是怎么生活的。”安妮娜解释,琉璃河遗址首次在北京的大遗址中建立了web-GIS地理信息系统,将遥感考古、坐标信息、航空摄影、电法物探、勘探和发掘的成果统一到大遗址“一张图”中,逐层进行绘图、摄像、建立三维模型,全面收集信息。考古人员完成了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米,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,遗址的保护区域范围为17.3平方公里,远超此前对遗址的认识。“总想要更多技工来帮忙,现在看来,这些男生能干的活儿,我们三个考古女队员干得也不错。”盛崇珊笑着说。
冬去春来,琉璃河考古工作站的小院里一片新绿。屋内,三个姑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文物的清理、修复、拼对,以及绘图、拍照等工作;很快,她们又将开启新一轮的考古发掘。今年琉璃河还会带来什么惊喜?三人相视而笑:“我们一起期待。”
链接
为3000年前的“乌龙”纠错
在M1901号墓,三个姑娘还收获了意外之喜。在该墓二层台的位置,她们发现了一只器形完整、纹饰精美的青铜簋。“里面会不会有铭文?”三人满怀期待。
给铜簋开盖的任务交到了年龄最小的盛崇珊手上。“这是我第一次给青铜器开盖。”戴上白手套,捧起铜簋,小心翼翼地打开器盖……那一刻手中的触感、激动的心跳,盛崇珊至今忘不了。三个姑娘凑在一起仔细观察,“有铭文!还很清楚呢!”这件铜簋的器盖内有6字铭文:“白(伯)鱼作宝尊彝”;进一步观察,在器内底也有14字铭文:“王祷于成周,王赐圉贝,用作宝尊彝”。
M1901号墓出土的青铜簋,器盖上的铭文清晰可见。北京日报记者 武亦彬摄
为什么器盖和器内铭文不一致?“同一件器物,盖与身的铭文应该是一致的。”王晶解释,一般一件器物只会出现一个做器者的名字,而这件器物出现了“白(伯)鱼”和“圉”两个名字,“这背后可能有故事”。
为了揭开谜底,她们翻阅了40年前“253号墓”的发掘报告,发现这里曾出土一件圉簋,与新发现铜簋的纹饰非常相近。“两件簋的盖、身铭文正好是相反的。”王晶告诉记者,在前辈的指导下,她们推断,当初下葬时,两件文物“盖”错了,也证明了白(伯)鱼和圉实为一人,“时隔40余年,两器重聚首,才解开这个一错3000年的‘乌龙事件’。”
采用“破壁发掘法”发掘的M1902号墓,可辨识其中随葬的青铜礼器组合及动物骨骼。 北京日报记者 武亦彬摄
还原古人随葬食物
最近几天,王晶和同事们正忙着对M1902号墓出土的器物进行室内清理和修复。实验室里,细小脆弱的动物骨骼碎片足有百余片,她们一点点拼凑起来,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动物考古领域的专家,为它们辨明“身份”。一件铜鼎,经过精细的实验室技术检测,队员们发现鼎的外侧包裹着一层织物,鼎中推断有一个木制的器盖,鼎底保存了几块动物骨骼,经过鉴定,这些骨骼是两块羊前腿和几块“羊蝎子”。
“随着实验室动物考古工作的推进,我们发现越来越多有意思的事。”王晶揭秘,通过对铜鼎的逐层“解析”,可以还原古人随葬食物的“讲究”,“相当于盛食器里煮好了羊肉,再盖上盖,最后用织物包裹起来入葬。”她们还在棺内头厢的位置发现了羊肋骨,上面有清晰的刀的划痕,经鉴定,和鼎内的羊骨来自同一只羊。
另外,动物骨骼中还鉴定出两只狗:一只约1岁半的狗在椁盖板上,戴着一只铜铃,据推测是墓主人生前的宠物;另一只小狗还未成年,体型较小,被放在墓底腰坑的位置。“这些是我们研究古人吃什么肉,吃哪个部位,有没有宠物随葬等当时祭祀和殉葬制度的重要依据。”王晶说。